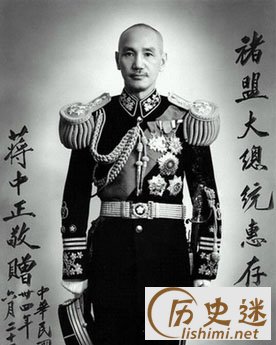南京大学出版社(书评)
□ 谷立立
在当今这个时代,旅行大约不是什么稀罕事。放眼身边,一心念着“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的年轻人已渐渐成为时下主流。不妨想象这样的场景:某个清晨,一个女孩独自坐上远行的快车,之后依次在巴黎、伦敦消磨时光。如果不嫌太过疲惫,她大可以走得更远,在苏格兰钓鲑鱼,到纽约吃晚餐……凡此种种,都不过是用自己越来越大的步子,去丈量这个越来越小的星球,重新诠释“旅行”的意义。就像法国作家保罗·莫朗在其随笔集《旅行》里所写的那样,“所有人都在路上,所有人都是旅客,留守的人反而变得特立独行”。
《旅行》,(法)保罗·莫朗著,唐淑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49.00元。
当然,莫朗并不想就此远离人群,呆在家中,刻意扮成“特立独行”的样子。对于旅行,他所知颇多。早在现代技术把地球变成小小村落之前,身为外交官的莫朗就已经把自己的足迹,印在了各个大陆之间。然而,《旅行》既不是旅游指南,也不是行走艺术。谁都不要指望莫朗会摆出一副“看遍了世间风景”的导师架势,亲自上阵讲解他的旅游攻略。说到底,《旅行》是一种“追忆似水年华”式的写作。莫朗既不效仿“到此一游”的潦草做法,更不寄望当下时代被裁剪、被压缩成薄薄一片的仓促行程,能为他带来多少愉悦。
相反,莫朗的笔下带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绅士特有的精致与优雅。当旅行已经成了“集体的迁徙”,他却愿意独自退回到过去,坚守他孤独的远行。他相信,最好的旅行是“向过去旅行”,向昨天旅行。因为,昨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昨天,壮美之景被珍重收藏;而今天,它们几近强制性地被展现在众人面前”。这意味着,旅行的意义不是见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水,而是在见山见水的路上,我们究竟发现了什么。
于是,我们读《旅行》,就像走进了莫朗的旅行主题博物馆。他在图卢兹-罗特列克、莫奈的画作中,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亨利·莫尼埃的短剧里,寻找过去年代的痕迹。很快,所有这些极具年代感的老物件,就像刚刚从蒙尘的旧画片上剪裁下来,就被他顺手拿了过来,以“旅行”的名义,摆在了展台上。不过,与任何一位对超现实主义抱有热情的艺术家一样,莫朗并不提供完整而系统的讲解。他自顾自地“沉到潜意识中去”,一会儿谈论着老爷车的性能,一会儿沉迷于公路的变迁,一边穿行在东方的集市里,一边追问“世界的尽头在哪里”,仿佛在酝酿一首超现实主义的诗作。
以东方快车为例。如果要给莫朗一个选择,他宁可回到1904年之前,与熙来攘往的异乡客一起,一边穿越喀尔巴阡山脉,“一边在粉色灯罩的微光下享用晚餐”,而不会像偷工减料的当代人那样,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横跨整个欧洲大陆,把节省下来的大把时间,用在无聊的自拍与肤浅的炫耀上,然后得意洋洋地告诉朋友,“我只用14天就游遍了欧洲十国”。显然,在过去的旅行中,“快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愉悦的体验。阿加莎·克里斯蒂没有说错。东方快车就是一本流动的百科全书,是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舞台。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天知道这样一个庞大而又落伍的古怪玩意儿里面,到底藏着多少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迹。莫朗还记得他曾经与一个罗马尼亚人同行。那时,他骄傲地告诉莫朗,1801年他的曾祖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撒满糖霜,只为了向对他的家乡一无所知的巴黎人展示如何搬动雪橇在雪地上自如地滑行。只是,随着东方快车退出历史舞台,一切就悄悄地改变了模样。莫朗甚至猜想,1913年在东方快车里安睡的亿万富翁大概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许多年后,当他们在快速飞驰的高铁上醒来,会不会发现自己正置身于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斯坦布尔快车》里,面对一系列并不属于他们年代的尴尬、惊悚,眼见着唠唠叨叨的酒鬼、碌碌无为的官员、卑躬屈节的走私犯……依次排着队从面前飘过,留下一长串“充满疯子的噩梦”。
这是小说家的想象,还是真实的事件,我们无从得知。或许,这正应了那句话“没有什么以文学开始,但万事皆以文学告终”。莫朗坚信,文学与旅行并不矛盾,伟大的作家往往是伟大的旅行家。一方面,他们极少“宅”在家中,挖空心思,等待灵感的降临;另一方面,长时间的旅行不仅不会让他们远离写作,反而会将他们推向书桌,拉近作家与笔下作品的距离。
这样的作家,被莫朗称为“痴迷远方的朝圣者”。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为数众多的朝圣者中的一员。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里,莫朗在有形的路上(旅途)与无形的路上(创作)之间做着双重的探索。终其一生,他以旅行“履行着自己的义务,逃避没有使他得到解放,反而把他卷入其中,迫使他负起责任。”于是,就有了一部部掷地有声的杰作。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无视莫朗的邀请,拒绝与他一道穿越时空,去见证旅行的黄金年代?因为不管时代如何改变,莫朗始终不会忘记他的使命;莫朗仍然是老派的精英,不顾世界的喧嚣,独守着记忆的美好。这种美好,是过去年代的赐予,更是“奥德修斯、蒙田、卢梭和夏多布里昂留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