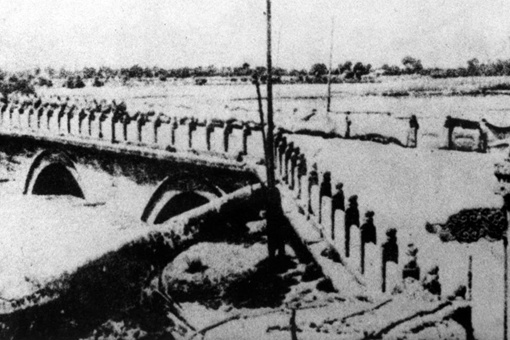哈佛大学录取分数线(如愿以偿的侥幸)
作者:王露橙,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InVisor & EdwithU 教育学留学导师。
2月23日,大年初八。这天起了个大早,准备乘动车赴武汉和高中老友聚会。吃早餐之际手机突然收到邮件提醒,是Penn GSE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告知我申请状态更新,请及时查看。心立刻悬了起来。屏住呼吸,颤着手,进入申请页面,点开Decision Letter(决定信),映入眼帘的是大大的“Congratulations! (恭喜)”。“我被宾大录取了…”听罢消息,妈妈这位少女比我要更激动,喜悦化作泪花蹦出来,急急忙忙跑到外婆房间,强忍着激动,低声把她唤醒。外婆鼓掌大笑,忙穿衣坐起,又赶紧到书房给家里供着的菩萨磕头。这是申请季接到的第一个offer,也是理想中的offer。喜罢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差些误了火车。
3月3日,年刚过完。这天也起得早,是返校日。睁开朦胧的睡眼按亮手机,屏幕显示收到了哈佛教育学院的邮件,睡意清醒了几分。但也不怎么抱希望的,点开了申请状态更新。
是飘着彩带的Congratulations。
“妈妈。妈妈。”她还在熟睡。我轻声唤醒她。
“我被哈佛录了。”
从高中立志出国,到如今被哈佛录取,有人说,这是付出终有回报。
而我深知这一切,是如愿以偿的侥幸。
我从高中就知道自己要去美国留学了,就跟我初中知道要高考一样。记得高三有一日上自习的时候,班主任把同学一个个叫出来谈话,大概谈高考理想志愿之类,以此勉励学生积极备考。当时的我对大学和专业一无所知,文不对题而又坚定地对老师说:“我大学毕业之后要出国的。”
我出生在湖北一个小城市,家境不算富裕,但也算小康。家里人很“重视教育”,身边的哥哥姐姐都走的是这么一条路: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出国读书。我从小被送到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班级,也算是听话争气努力学习,只是从来没当过第一。当然,初中是有过一次的,后来妈妈就觉得那个班太差,把我转到了另一所中学一个八十人的“重点班”。中考前,我以微弱的优势过了省重点高中校招考试的分数线,离开家乡,去省城武汉读书。这所超级中学一个年级有三十个班,同学们都是各市县选拔上来的尖子生,竞争愈发激烈。从小到大,我向来觉得自己是不如人的。哥哥姐姐永远走得比我远,飞得比我高;身边也都是极其聪明伶俐的同学。不过,我也并没有因此放弃——我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会做最努力的。笨鸟先飞,勤能补拙。
那好,那就去努力。
朝着明确的高考目标,高一入学便开始规划、积累。然而,到了高三,备考复习似乎并没有因为高一高二的努力耕耘而轻松。高考的日子愈近,考试焦虑愈发明显,睡不着觉是家常便饭,彻夜失眠也不足为奇。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三下学期出现了大幅下滑,从第二名,十名,五十名,到一百多名……越是下滑,越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考得不好是因为不够努力,要更努力才行。于是,课间十分钟、午休时间,所有除上课之外的零零碎碎分分秒秒全部用来背书,看作文,做习题。可紧绷的神经终于还是在高考那天脆断了,在又一次彻夜失眠后——
我填错了高考文综的答题卡。
高考分出来之后,来自各方的短信电话不停轰炸。我低头坐在一边,心烦意乱、漫无目的的翻看着志愿填报指南;妈妈强装笑颜,敷衍着电话里来者的关心。分数出来后,我和同学作伴出去旅游散心,朋友们都带着自己的妈妈,除了我。我的妈妈失意地待在家里,说没有心情。
侥幸的是,那是高考改革自主招生刚开始实行的几年。我通过了北师大的自主招生考试,获得20分降分录取。这才被教育学部招了进来,误打误撞读了教育。
就这样,我总算是和哥哥姐姐一样去读重点大学了。下一个目标,是四年后的赴美留学。围绕留学这个目标,要在大学拼命努力才行。
在进大学之前,就听已在美国读书工作的哥哥姐姐分享留学经验,陆陆续续知道了托福GRE、GPA、推荐信等。于是一进大学,便抓住一切机会提升英语:选外籍教授授课的专业课,用英文完成论文作业和读书报告,选外文专业的英语学术写作课程。也会有觉得困难的时候,但会暗暗对自己说,“你是要出国留学的人,最基本的英语都说不来,写不来,怎么和美国本土人一起学习!”想到这里,便又咬牙坚持了下去。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我每天早上给自己安排15-30min的早读时间,背新概念、Ted Talk、英语新闻、演讲、单词书;走路时间听NPR、VOA、BBC等英文广播;校内的外籍专家讲座我也绝不错过,在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逼自己举手,从一群硕士博士生中站起来向专家提问,提心吊胆地锻炼着自己的口语。通过两年见缝插针式的英语学习,我在大二下学期拿到了托福110(满分120)的成绩。与此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的一些留学讲座,进一步清晰了留学申请的时间规划,以及海外交换经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和科研经历的重要性,并为此做出相应准备。
这样看来,我的路好像无比完美、清晰与顺畅:早定目标,明确方向,提前准备,付出努力。的确,比起大三才决定出国,慌慌张张开始准备标化考试的一些同学,我的留学路走得更为从容:大一专注提升英语,收集留学信息;大二开始浏览申请学校及项目信息,了解学校院校要求,考出托福高分;大三用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语言成绩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交换生机会,在交换期间对顶尖名校有进一步的实地了解,最终确定选校名单,也顺便联系好了美国教授作推荐人;大四开始前,我完成了所有标化成绩的准备,然后写文书,填写网申,提交,最后被哈佛录取。良好的英语基础让我在浏览每个院校网站信息时毫不费力,从而省去了请中介的一大笔钱;考GRE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要申请的学校名单,在寄送成绩时省去了部分学校的成绩寄送费。出国留学这条路,我从未质疑,就像我从未质疑过高考一样。
然而,这只是故事肤浅的表面。
北师大的教育学部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大二上学期我申请更换导师,到了国际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滕珺老师的门下。在滕门, 我受到滕老师不少指导与帮助, 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并遇到了对我大学四年影响最重大、最深远的一个人——高我一级的万心珂师姐。 我叫过很多人“师兄”“师姐”,但真正能配得上“师姐”这个名号,既能做我老师,又能做我姐姐的,她是唯一。
初识师姐是在大一下学期。那时候旁听国家奖学金答辩,大二的心珂师姐在评委老师面前闪闪发光:成绩名列前茅,获奖无数,英语水平超群,修读教育学部外籍教授的研究生课程,赴美发表会议论文,还主管教育学部所有留学生的联谊活动。大二入滕门,惊喜地发现师姐也在,便鼓足勇气加了师姐的微信,想请教出国留学事宜。没想到立刻受到热情的回应:“中午小西门,师姐请吃饭”。第一次正式见面,师姐竟毫无保留,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上大学来的种种感受,从选课到科研,从交换生项目到出国留学,不一而足。心,倏地被这样一颗炽烈的心而温热。从此之后,我便和师姐成了至交。我们相约吃饭,运动,看电影,聊学业,聊出国,聊人生。我们有相似的背景,共同的目标,而师姐又在前方经历着自己即将经历的路。大学的路不再像高中那样明晰,前方的路都需自己慢慢摸索;而师姐的出现,无疑像一座灯塔,在人生未来的茫茫大海中,为我指明了方向。
然而,这座灯塔,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折断了——因为现实因素,师姐赴美留学的决定摇摆了。那时,我们的话题从去哪个大学,哪个项目,忽而变成了——是出国,还是不出国?
这样的转变对她是颠覆性的,对我亦如此。我从未质疑过出国这条路,就跟我从未质疑过高考一样。
等等,所以,出国还是不出国这件事,是可以选择的?事实上,就算是决定出国,也面临诸多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
以及在这背后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出国?
从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再到出国—— 从小到大的人生,我循着哥哥姐姐的路努力着,但我从未做过什么选择,生活也从未容我想过这样做是“为什么”。
我的方向在哪里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奋不顾身,克服万难也要实现的,是什么呢?能让我持续思考,乐此不疲做下去的,又是什么呢?能一路读重点,最后出国留学的人千千万,我又为何成其为我呢?
这些问题轰炸而来的时候,已临近大三,我也申请到了大三下学期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海外交换项目。按照之前的留学规划,此时已是出国留学准备的最后关键期了。然而,之前对留学的认识被全盘颠覆,我犹豫于那条理所当然的路,茫然于林林总总的选择,并意识到自己一直忽略的经济问题——父母从不愿让我为钱担心,但硕士留学费用显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久违的焦虑又翻江倒海而来,彷徨与紧张交加,击溃了脆弱的心。
我去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老师说,你不如先暂停一下。一切都还来得及。
大三上学期,我将信将疑地推掉了一些学生工作和实习。生活从未过得如此轻松,神经性的头痛与失眠让我无力顾及课业外的其他。而对即将开始的海外交换生活,我竟一度丧失了之前所有的期待,只是茫然地担心自己能否顺利活过在异国的四个月。
这四个月,你就好好休息吧。师姐对我说。才发现,从大一到大三,我主动地忙碌着一切的一切,却几乎从未主动休息过。
2017年1月某日,飞机降落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我单击word文档的“保存”按钮,合上电脑。美国的春季学期开学很早,他们不过春节。师大这边,几周之后才正式放寒假,大三上学期的课尚未完结。我只能向老师申请提前进行期末考试,并在旅途中完成剩下的期末论文。一切就这样慌张的开始了。
来到大洋彼岸的异国,每分每秒都是那样崭新,应接不暇的新鲜感让我更专注于当下。从“追求卓越”的条条框框中跳脱出来,作为一名国际交换生,我不必与任何人争抢。反正眼前的生活已经糟糕成了这个样子,反正我这个人在美国大地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四个月,放飞自我就好了。破罐子破摔,潇洒一些。
放荡不羁爱自由, 又哪里有如此简单呢。
“如果爱一个人,请送她去纽约;如果恨一个人,请送她去纽约。”纽约这个大都会,有西装革履的华尔街精英,也有落魄的地铁流浪汉;有高调奢华的第五大道,也有山寨满街的中国城。好奇的本能被激发、放大,但保守的惯性却闭锁了向外探求的心。明明想去和人交谈,却怎么也不敢开口,担心听不懂,接不上茬,错误百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也无不“处处小心,时时留意”——美国人的常识于我而言是崭新的知识,我只能像一个婴儿一样,一切从头学起。无知的冒失不时招来冷眼相待:叫不出菜名,只能用手指点,却被食堂阿姨咕哝了几句听不懂的英语;排队买东西,却发现前面的白人老头满脸厌恶地避开我站到了队伍的另一边。也不知是自己的玻璃心,还是美国的大环境,总之,慢慢体会到身为少数族裔(minority)的滋味;无奈之下,也只能用微笑来掩饰尴尬,表示友好。
所幸在学校的大部分体验是开心的。之前在国内对美式教学已有提前的适应和了解,也慢慢恢复儿时的“任性”,凭“喜好”做出选择。授课教授中有一个亚洲面孔——韩裔美国教授Lisa Son,宾夕法尼亚大学本科,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现任巴纳德心理系主任,教授认知心理学课程。与国内冗长的大讲堂不同,Lisa上课,允许学生随时打断并提问,讲授深奥的心理学理论时,也会插入丰富鲜活的实验和事例增进我们的理解。几节课后,我预约了她的office hour与她私聊。我用不怎么熟练的英语介绍自己,谈及自己焦虑的过往,糟糕的现状,以及迷茫的未来。我说,也许美国的教育会更人性化,让学生在选择中张扬个性,不至于像中国学生一样,光知道千篇一律的盲目竞争。
“你知道吗,我宁愿回韩国接受那样的教育。”她于是讲起了自己的过去。成长在亚裔受严重歧视的年代,学生时代的她遭受着各种霸凌,很多时候只能在厕所吃午饭。从小到大被排挤的孤独,让她焦虑、惊恐,甚至成为日后癫痫病的触发源。我愣愣地听着,对这个发达国家的种种美好幻想刹那间被击碎,碎片割破心脏痛到骨髓。伴随着久久不能平静的心情,我给她回复了一封长长的邮件,感谢她那么坦诚地向我分享她的过去,并让我看到了一个此前从未知晓的美国。我随后加入了她的认知实验室,辅助她做少数族裔的元认知研究。之后的时间里, 我们也有了更多的交谈。她像心珂师姐一样,那样炽烈地回应着我,讲述她是怎样从自卑慢慢走向自信,怎样学会与自己坦诚相待的。我是那样敬佩她。在那样光辉的外表下,是痛苦和不堪的过去,更是拨云见日的通达。
在巴纳德还选了一门英语写作课,老师没讲任何学术写作相关的东西,而是让我们写个人经历(personal experience)。题目自拟,内容自定,结课方式是完成自己的“作品集”。我于是开始“不羁”地写,写我的进食障碍,写我的焦虑失眠,写那些不愿为人知晓的伤疤。我把文稿打印出来,在课上共享给大家讨论,反馈意见——这也是课程的一部分。在包括老师在内的十二人小班里,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大家接纳了这样“残缺的我”,对我的文章给予写作上客观的评价,鼓励着我,并意外地,向我分享他们相似的经历。
某日阳光正好,全班到楼外到草地围坐上课
写作课成为了我疗愈的过程。在众人的启发与自我的反思中,我意识到自己“追求完美”的思维定式。完美意味着成功与确定,而不允许失败与变化的出现。害怕失败,因此无法鼓起勇气对外国人说英文;按照“完美的规则”去规定自己的饮食搭配和睡眠时间,反而忽略了身体最真实的感受;更因为对确定性的过分追求,在面对选择与未知时,表现出恐惧、焦虑,却并未将这视为可能与发展的空间。讽刺的是,在美国的这几个月,失败和尴尬是生活的日常,现实生活也总是充满着不确定——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必然。作品集的最后一篇文章,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A Letter to Myself)。我说:“我一直把“你(自我)”包裹在襁褓里——不让任何细菌接触,不冒任何风险,保持绝对的安全与纯洁。殊不知,不让你去泥里滚,雨里爬,不让你生几次病,你便永远无法获得免疫力,健康成长,并去往更大的世界。”更何况,我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残缺”,每个人都有那样柔弱的部分。高高在上的教授也是,身边优秀的同学们也是。脆弱,失败,不安,痛苦,那些消极的一切,无法避免,也无需逃避。它是让自己强大的力量,是共情的开端,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开始。
我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我是最独特的。
申请哈佛的时候,我把给自己的信作为附加材料传了上去。
找不到方向的时候,看同辈正在走的路,看长辈走过的路,也别忘了,回头想想自己来时的路。
我的“完美”和“忙碌”在大洋彼岸暂停了四个月。这四个月里,我狠狠地去反思教育与学习的意义。“重视教育”的父母为我规划好了近五分之一的人生,但在计划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难以预见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多元开放的选择,更无法想象我二十岁之后的职业生涯。难道家庭教育,就应如此吗?学校教育呢?学校在象牙塔里培养一批批“完美”达标的学生,等他们走出学校面临社会的变化与选择时,抑或茫然不知所措,又或忙碌奔波,而不知意义在哪里?可是,学习的真正意义难道不在于此吗——人凭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在实践中发现了种种问题;因想要进一步探究并解决,所以开始学习前人的各种知识,并加以自己的思考。最后,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通过与他人合作、努力,让社会进步,让世界美好。知晓这样意义的学习者,定是一个主动积极、热情昂扬的终身学习者。她的学习动机,源自对这个世界本能的好奇,源自对知识真正的渴求,源自与全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担当。
如何培养自主的终身学习者?当我开始梳理从高中到大学的经历时,发现自己做的事里多多少少都与自己的经历相关:大一的教育学课上,我写了一篇关于高考利弊的论文;大一下,我与母校一位高三的学妹保持每周联系,用教育心理学的知识帮助她调整心态,用“选择”的态度明确未来方向。最后,她高考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上了人民大学她心仪的专业。大二带志愿者社团的时候,我联系更多大学生与欠发达地区高中生结成对子,复制我和学妹的形式开展朋辈咨询。我之后又有了很多新鲜的经历,但这个问题总会不时浮现出来,让我乐此不疲地思考着,实践着。纽约的高中课堂上,学生的主动性如何?中国的农村青少年在自主性方面又呈现怎样的状态?当下的大学生,在面临选择的焦虑和迷茫时,是否能通过朋辈帮助他们找到方向,一如师姐于我那样?
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毕业之后去工作,去实践,发现问题,再去有目的的深造——这也是大多数国外人走的路。我们在象牙塔里太久了,对知识——这实践经验的精华——丧失了最原本的体验与敬畏。真正的学校不是哪个顶尖名校,而是这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中反思,反思中实践,在书本里与前人去对话,在实践中与现世去对话,才能发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感受到内发而持久的快乐。
2018年,3月3日,我收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士录取。
从高中立志出国,到大四被顶尖名校录取,有人说,这是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但我深知,我在大学差些被焦虑打倒,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才刚刚起步,实践经验也寥寥无几,也还面临着无知的未来,与无尽的选择。硕士学习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gap year(间隔年),在异国他乡开阔视野,找寻更多可能的机会与发展的空间。
我说这一切,是如愿以偿的侥幸。
作者:王露橙,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InVisor & EdwithU 教育学留学导师。
上一篇:齐齐哈尔大学排名(最新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