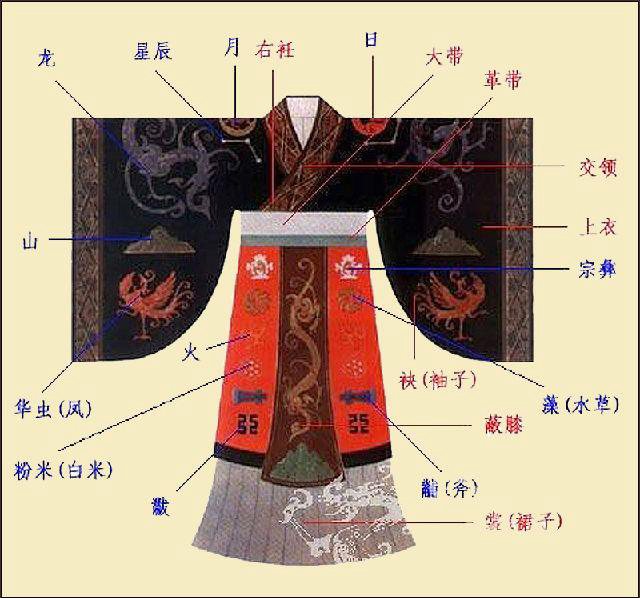民工刘二插大学生(故事连载14)
一个重大消息,两个特殊人物
朱元璋的故乡古称钟离,元代升为濠州,明代改称凤阳。它是淮河流域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除了淮河两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在史籍中偶尔露一下面外,很少有人提到它。但朱元璋的发迹使凤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三月,一个重大消息传到了南京:朱元璋的故乡濠州被朱军攻占。
朱元璋的心情异常激动。从军之后,他只有至正十三年回钟离招过一次兵,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如今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十几年戎马倥偬,日日夜夜精神高度紧张,他似乎已经忘了故乡的存在。然而消息传来之际,朱元璋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其实无时无刻不挂念着那片贫瘠的土地,毕竟,他二十五岁以前的所有记忆都存放在那里。
生存斗争的压力抑制了他对故乡的热念,如今全国大势已经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气了。接到故乡收复的消息,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同洪水决堤,居然一发不可收拾。故乡记忆在脑海中一下子全面复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闪过。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攻下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
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朱元璋从南京起身。随从的还有两个特殊人物,一个叫刘大,一个叫曹秀。
父母坟前
刘大就是慨然送地,使自己得以安葬父母的刘继祖的儿子,曹秀则是当年拿出自己所有家底置办礼品送他入皇觉寺为僧的汪大娘的儿子。他们是朱元璋终身难忘的两大恩人。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已经成为红巾军镇抚大将,这年年底,他在濠州城意外地见到了前来投奔的刘大和曹秀,惊喜非常,说“吾故人至矣”,忙问刘继祖夫妇和汪大娘的情形。原来汪大娘在朱元璋投军不久就去世了。到至正十三年初,刘继祖也病故了,家里只剩刘大一人,年小力薄,遂和曹秀一起来投奔。朱元璋闻听,“惨怛动容”(《凤阳新书》,《刘继祖传》),留下他们作了自己的贴身护卫。虽然二人才能平庸,不堪大用,朱元璋对他们却一直另眼相看。两人屡次请缨到前线作战,朱元璋都没有同意,说,我不会让你们冒生命危险,那样对不起你们的父母!
这次回乡,朱元璋特意带上这两个人。除此之外,他还特意带上一名博士官(许存仁)和一名起居注官(王祎),来记录他这次必将载入史册的“太祖还乡”。原来的流浪和尚现在已经成了即将登上帝位的“吴王”,这种巨大的身份变化使这次回乡一定比普通的衣锦还乡更具戏剧性。
刚刚上路之际,他还想摆设全套吴王仪仗,可一出南京城,他已经心如归鸟,把仪仗甩在身后,命令士兵日行百里,仅用三天,就奔到了故乡。
跨过村边那条小河,村头那棵老白杨还在,可其他都已经面目全非:村边那座规模不小的皇觉寺,而今只剩几条低矮的残墙和数堆瓦砾。村中一座座房屋倾坍破败,原本一百多家的村庄,而今只有二十多户还有人烟。自己家的老院子里,荒草已经近人高,三间草房,早已塌了顶落了架,朱元璋一行人的接近,只惊起了一窝鸦雀。
朱元璋内心一阵酸痛。
二十几户乡亲被马蹄人声惊起,战战兢兢地在门口向这里张望。在确定这不是一伙劫掠者后,人们渐渐聚集到了朱元璋家的老院子里:一个个鸠形鹄面,面带胆怯,衣衫褴褛。
朱元璋首先认出了小时候的玩伴刘添儿。添儿比自己大两岁,今年应该四十二,看起来却像是五六十岁的光景,腰弯背驼,面目黎黑,瘦得如同一具骷髅。小时候,刘添儿处处关照他,在自己吃不饱的时候,经常掰给自己半个饼子。如今,竟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朱元璋眼眶湿润,向他走过去:
“添儿?是你吧?”
刘添儿满脸迷惑,朱元璋说:“我是重八啊!”
“重八?”“重八!”“啊呀,重八回来啦!”……乡亲们一下子爆炸了,奔上前把朱元璋围在了中间:“这谁敢认啊!重八,你这是做了大官儿啦?”
朱元璋拉着一双又一双枯手,半天不能言语。终于平复下来,能说话了,嘱咐身边的侍卫:把你们带的干粮干肉都拿出来,给乡亲们分了,把带的那些礼品也给大家分了。
二百多名士兵的行军粮分给了二十多户人家,每家还分到了朱元璋从南京带来的两匹绸子,两匹棉布。那个时候,棉花在中国尚未普及,因此也是珍贵礼物。此外,每家还分到了二十两银子。
青黄不接时节,许多人家已经吃了一个月野菜,此时许多孩子当着朱元璋的面就大口大口吃起干粮来。整个村庄都一片喜气洋洋。
朱元璋却高兴不起来,衣锦还乡的自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没有料到战争把家乡破坏得如此彻底。趁着大家回家生火做饭,他带着随从到村外去给父母上坟。
坟地几乎已经找不到了。朱元璋记忆中堆得很高的坟头风吹雨侵,已经几与地平,荒草连天,大地寂静无声。朱元璋想着躺在地下的父母,可惜赶不上他今日的荣华了。他跪在低矮的坟头前,泪如雨下。
他本来想把父母的遗骸起出来,找个好地方另葬,但是博士官许存仁和起居注官王祎极力反对。他们说主公能有今日,显然是因为父母的坟风水好,要是起坟改葬,恐泄山川灵气。朱元璋一听有理,于是下令就地培土,“增土以倍其封”。
再回到村子,乡亲们已经从留在村中的侍卫那里知道,如今的重八,现在已经是“吴王”,不久之后就是皇帝。再见到朱元璋,大家扑通一下,都跪了下来。朱元璋命大家起来,他们起来后也都面带拘谨,不敢说笑了。朱元璋和他们细话家常,问他们这些年的境况,才得知村中人一多半儿死了,剩下的也都逃走。濠州的战争刚刚停止,大家都指望今年能过个太平年。
朱元璋宣布,任命和自己同来的刘英与曹秀为守陵官,全权负责守护皇陵之责,又宣布赐给这二十户乡亲每户视人口多少二十到三十顷地,免十年钱粮。朱元璋说,你们这二十户,以后就不用种地了,地佃给别人种,你们专门帮我看守祖坟,我立你们为陵户,帮我照料祭祀之事,不要你们出钱,祭祀过后的猪羊,就给你们吃了!以后你们每日间,只要收收租子,吃吃酒,快快活活度日罢!
大家又纷纷趴到地下,结结实实给朱元璋叩了几个头。
朱元璋环顾乡亲,发现和刚才比,少了一人:前地主刘德。
当年仇人刘德
从南京出发之前,朱元璋头脑中就一直在想,那个刘德如今怎么样了?
在刘德家里叩头求地的情景,是朱元璋生命中最大的耻辱。
刚才那二十多户之中,他注意到了刘德。当年那个精壮富态的刘德,如今也已经苍然老矣。在那时的朱元璋眼里,刘德就是村中最大的成功人士,举手投足,派头十足,让朱元璋十分敬畏。如今看起来,不过是个又老又猥琐的没见过世面的乡间老头。
听到朱元璋如今已经是吴王,刘德心里忐忑起来。朱元璋再次回村,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朱元璋派人把他叫了过来。大家心里都紧了一下。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朱元璋这些年,可是以杀人为业。
刘德跪倒在朱元璋面前,一边磕头一边口中叨念:主上开恩,恕小的当年有眼不识泰山吧!可怜小的如今也一把年纪了吧!
朱元璋亲自上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你不用害怕。当年之事,我不会计较。“此恒情耳,不必问。吾贫时,尔岂知今日为天子耶!”(《国榷》卷一)嫌贫爱富,这是人之常情,我不和你计较。那时候你怎么知道我会当天子!同时还宣布,赐给刘德三十顷田。
在场之人,无不为朱元璋的宽容大度所感动。起居注官忙把这段话记载下来,他知道,这必将成为一桩历史佳话。
其实这一刻的一举一动每一句话,朱元璋在离开南京前就筹算好了。
朱元璋处处模仿汉高祖刘邦,对刘邦样样都佩服,但是对刘邦“羹颉侯”一事,却一直大不以为然。
由贫贱起身的人,总有相似的尴尬。年轻时的刘邦喜欢带着酒肉朋友到哥嫂家蹭吃蹭喝,喝酒吹牛。时间长了,嫂子难免不愿意。有一天,刘邦和一帮小兄弟走进家门,却听到嫂子拿锅铲狠狠铲锅的声音,那意思是告诉他,锅里没饭了,到别处去蹭吧,把刘邦弄得脸没处放,从此便留下了“击釜之怨”。当了皇帝之后,他大封近亲为王为侯,但唯独就是不封大哥大嫂的独子刘信。直到太上皇刘瑞亲自说情,刘邦才决定封他为侯,但在下旨时,却颁了一个刻薄的封号:“羹颉侯”。“羹颉”之意是“饭没了”。
即将开国的朱元璋,期望着以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形象进入历史,因此他对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都很重视。朱元璋认为:“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五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则度量亦未弘矣。”也就是说,刘邦本是宽怀大度之人,却因为这桩小事破坏了形象,十分不值。帝王形象无小事,越是戏剧性的小事,越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环节。
在离开家乡前,朱元璋命人从外面采买食物,请乡亲父老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史载朱元璋在宴会上向乡亲们发表了如下重要讲话:“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并嘱咐道:“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自爱,以乐高年。”据说乡亲们异口同声答道:“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
穷乡僻壤差点成为首都
朱元璋对家乡的情感确实非常深厚。他就是凤阳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棵植物。在戎马倥偬之中,他时刻感受着人性的冷酷,但是一旦回到这贫瘠的故乡,他马上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熨帖,那么踏实。故乡那熟悉的一草一木和乡亲们对他的真挚情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然“子宫”,让他在这里感觉最安全、最舒服。
洪武元年,大明开国,定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然而不久之后,朱元璋就提出一个令大臣们十分震惊的计划:把帝国的首都设在老家凤阳。
开国前后,关于新帝国的首都,君臣们进行过多次讨论,因为南京在全国的位置偏于东南,所以大臣们提出过长安、洛阳、开封和北平等方案。这四座城池都是历史名城巨镇,各有优势,当得起首都之任:“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
没想到朱元璋却提出,在凤阳建设中都。他说,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凤阳则离中原很近,而且“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实录》卷四五),以之作为中都,可以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
除了淮西籍的功臣们赞同外,其他大臣们都面面相觑。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小地方定为首都,这实在有点太匪夷所思了吧?凤阳经济落后,又“平旷无险可守”,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定都之地。性格耿直的刘基直接对定都凤阳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
然而朱元璋听不进去。大家也就罢了,他们深知他说一不二的性格,主子定了的事情,除了服从,还有什么选择呢?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罗列论证了那么多,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
于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九月,朱元璋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在朱元璋的设想中,自己的故乡将成为未来的正式首都,南京将降为陪都。农民虽然生活节俭,但修宅院总是不惜血本。同样,朱元璋一贯做事节俭,这一次却不惜血本,他要倾全国之力,高标准严要求,要把中都建造成万年不易的金汤之地。所以中都从设计之初就务求雄壮华丽,他要求选取最好的材料,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
经过百万民工六年日夜不停的建设,一座座雄伟的宫阙相继拔地而起。
朱元璋的要求在各个环节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考古学家后来在中都遗址中发现,中都残存石构件的数量、品种、质量都远超过元大都。大殿蟠龙石础每块都是2.7米左右见方、面积超过7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其气派远胜过历代首都。后来明成祖修建北京城,金銮殿上的石础体量只有中都的三分之一。
现在中都石构部件的所有外露部分,全都精雕细刻,花费了巨量人工。
历史上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城凤阳一时成了明帝国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有里外三道城垣,三城相套,布局奢侈宏阔。宫城(大内)城垣“周六里”“高三丈九尺五寸,女墙高五尺九寸五分,共高四丈五尺四寸五分”。皇城周长“十有四里”,砖石修垒,“高二丈”。最外面的中都城城垣“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用土夯筑,“丈高三”(当为“高三丈”),气势极为雄伟。为了使这座城池垂之万世,朱元璋还要求在城墙关键部位灌注熔化的铁水,比如“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熔灌之”(《实录》卷八三)。
洪武八年,工程基本完竣,朱元璋又一次亲临凤阳,验收工程质量,“验功赏劳”。然而在参观完这座耗尽了全国物力的雄伟新都之后,朱元璋却又作出了一个让全国惊掉下巴的重大决定:废弃中都!
原来,在这次验收中,朱元璋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因为劳动太苦,又不给工钱,那些被迫调来兴工的匠人心怀不满,实施了“厌胜法”,也就是我们说的“下镇物”,在宫殿的一些关键部位,埋下了咒符、泥人、木人、弓箭、剪刀、纸人等东西,据说这样将给居住者带来噩运。建筑已经完成,要想清理出这些镇物,十分困难。
《明史》卷一三八对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有厌镇法。”
也就是说,在验收工程的时候,朱元璋坐在新修成的宫殿中,却隐隐约约听到似乎有人在殿脊上拿着刀枪打仗。他询问怎么回事,李善长奏报说,有人对这座宫殿“下了镇物”。
朱元璋的反应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明史说他“将尽杀之”,也就是把修造宫殿的所有几千名工匠全部杀掉。工部尚书薜祥冒死进言,说只有木匠才能下镇物,铁匠和石匠没有责任,“活者千数”,一句求情,救活了一千多人。
就因为这一件偶发之事,导致了中都城全部作废。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在大明王朝却是天经地义:天下者,帝王之天下也。他的意志,是国土内唯一的意志。难道你以为他会为了珍惜一百万工匠六年的劳动,而生活在将造成自己心理障碍的建筑中吗?
朱元璋的报恩方式
生活在老家的想法破灭了,但是朱元璋对自己的老乡,却从来不改亲爱之情。对别人,他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是杀人如麻的魔鬼,但是对老乡,他却始终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重八”。
开国不久,他正式任命刘大、曹秀为从仕郎,专门守护皇陵。还特意为他们改了名。刘大之名当然不能进入诏旨,他特别改为刘英。曹秀则连名带姓一起改了,叫做汪文。
何以把姓也改了呢?原来汪大娘有子三人,为了报恩,朱元璋特令曹秀改姓为汪,以示对汪大娘的纪念。其他二子,继承曹氏香火,依然姓曹。所以凤阳民间至今有“洪武改姓,曹汪一家”之说。六百多年过去了,凤阳曹汪二姓之间,仍有不能通婚的习俗。
洪武七年元月,朱元璋专门设立皇陵祠祭署,于是汪文、刘英的官名又改为了“皇陵祠祭署署丞”和“署令”。汪大娘的另两个儿子,一个被安排为祠祭署中层官员,另一个被封为卫所指挥。汪大娘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这一年六月,朱元璋又特意把恩人的第三代,汪文的儿子汪伦,刘英的儿子刘鉴,送到南京国子监读书,“日给糈脯,冬夏给衣布等物”(《凤阳新书》卷二),照顾十分周到。
及至洪武十一年五月皇陵完工之时,朱元璋又宣布,将刘继祖追封为义惠侯,特命将刘继祖夫妇、汪大娘,还有村中一位朱元璋小时候叫干娘的赵氏神主配在父母陵寝,享受皇家烟火祭祀。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洪武年间,别的大臣见了朱元璋,都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只有他的老乡们,在朱元璋面前一直大大咧咧,不拿自己当外人。洪武中期,刘英有一次从家乡跑到南京来看望朱元璋。朱元璋因有事在身,三天之后才召见,官员却找不到刘英了。找了好几天,才知道刘英不耐烦等着,已经回凤阳了。朱元璋请刘英再进京,不料刘英觉得朱元璋摆架子,不高兴,居然一直没动身。如果是别人敢这样做,朱元璋一定会灭了他九族,但是对刘英,朱元璋却感觉很抱歉。只想着怎么把刘英请来,却传来消息,刘英突然病故。朱元璋深感悲恸,特意写下了《祭署令刘英》:
昔者朕寓居是方,存亡者感英父子之恩,至今犹存情怀,未尝有所忘也。
前者英赴京来,朕为机务浩繁,兼寿有年,失顾问于英,三日复觉,令人觅英所在,莫知所之。稽于金川之门守者,报无知英之出入。
复于京内物色数日,乃知英还矣。命召复劳再见,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云英亡。
呜呼!感恩之道常怀,感恩之礼未终,英遽然长逝,朕思昔恩,不胜嗟悼。特以牲醴之奠祭之。英其不昧,飨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八)
朱元璋的御制文集,篇数本不太多,关于汪刘两家的圣旨,竟然多达五篇,可谓绝无仅有。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他杀戮殆尽,只有汪刘二姓,不但洪武一朝享尽荣华,甚至终明之世,都世袭为官,朱元璋的报答,可谓情深义重了。
大明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
朱元璋回乡所见到的二十户老乡,后来成了大明帝国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被朱元璋立为陵户,不用下地干活儿,坐享国家补助,并且子孙世袭。
朱元璋在制定了天下各阶层礼仪制度后,还特别规定,这二十户陵户建房,可以用官员用的红色。所谓“无贫富,皆赐朱户复其家”。数代之后,有的陵户家庭破败下来,住进了“茅屋柴扉”,然而“上犹施朱”(沈士谦《明良录略》)。
洪武二年,凤阳大规模修建皇陵,因为工程阔大,陵园圈进了许多乡亲们的祖坟。按历朝定制,这些普通坟墓都要迁出皇陵陵园另行安葬,不得混于皇家陵寝之中。朱元璋却特批不用迁动,还允许他们随便进入皇陵祭扫:
“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春秋祭扫,听其出入不禁。”(《朱元璋与凤阳》)当听说乡亲们有人生活贫困之后,朱元璋还会赐给他们银钱土地。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他“赐皇陵祠祭署令汪伦(此时汪文已经去世,由汪伦接班)及守陵人七十七户钞有差。先是,上以山陵之故,命给伦等田地,以优眷之”。
朱元璋对老乡们说话,从来都是直截了当,如同与自己的家人聊天一样。有一次,汪文汇报,想在自己署内多设几名吏员,也让老乡们的孩子有份好工作。朱元璋没有同意,特意下圣旨说:
昨日,汪署令奏讨吏,我不与他。吏多生事害人。好人家子孙做了吏便害民。你陵户中间拣选识几个字的点得人名便罢。你陵里有甚么大事?一年祭祀,止轮一遭,将的猪来祭了吃了猪去,将的羊来祭了吃了羊去,钦此。
在南京皇宫宴请凤阳老乡
自从洪武八年发生了“厌胜事件”后,朱元璋再也没回过凤阳。不过,他却时时思念凤阳老乡们。毕竟,这二十户乡亲,就是他与凤阳联系的血管,通过他们,他才能感觉到故乡的体温。
洪武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已经步入老年的朱元璋突然非常想念老乡们。
于是命人将二十户乡亲请到南京,一是以慰相思之情,二是也让他们来首都见见世面。几天之后,老乡们都进了城,却先派人向朱元璋奏报,说是大家衣服寒酸,见不了天子。
朱元璋听后大笑,命尚衣监太监,从自己的御用衣库中给每人挑衣服一套,靴、帽各一件,把他们安置到本来是专门接待外国使臣的会同馆休息。
第二天,老乡们进宫,与朱元璋相见。朱元璋与大家一个个拉手叙了家常,又在奉天殿左庑摆开宴席,大宴乡亲。饭菜十分丰盛,内容都是乡亲们见所未见,吃完之后,还剩了一大桌子。看着老乡们一副舍不得的表情,朱元璋命人把饭菜用捧盒打包,用“黄龙袱”包好,给他们送到会同馆,让他们晚上吃。
第二天朱元璋又请大家进宫,放下工作,亲自做导游,领着他们逛皇宫的一座座宫殿。对乡亲们来说,这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朱元璋还让他们见了皇贵妃(此时马皇后已逝),然后又大摆宴席,和大家痛饮了一回。
第三天老乡们回家,朱元璋赐每人五十贯钞。皇贵妃也赐每人五十贯,还每人送了一斤苏木、一斤胡椒。朱元璋亲自把他们送出了西长安门,手把手叮嘱他们爱惜身体,一一惜别。
送走乡亲们之后,朱元璋却感到无限伤感。乡亲们年纪和自己差不多,都六七十岁了,但是身体一个个却差得多,这一趟虽然开了眼界,却有好几个累病了。因此他当天发下诏旨:
凤阳亲邻二十家,老的们路途遥远,江河雨雪不便,今后不必来了。教他家里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教训子孙读书,休惜课钱,遵奉乡饮酒礼。东鲁山,西鲁山,马鞍山,万岁山,都与他,教儿孙鞍马出入,行鹰放犬,采猎打围,弓箭我都不禁他们的。(以上俱见《凤阳新书》卷五)
皇子教育基地:凤阳
虽然凤阳没能成为首都,但朱元璋的崛起,仍然使它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
早在吴元年收复濠州后,朱元璋马上升濠州为临濠府。为了配合兴建中都,洪武四年,朱元璋扩大濠州的辖地,使临濠的领地由四县一下子扩展为九州十八县。洪武七年又更名为凤阳府,这一新府管辖亳州、颍州、太和、颍上、霍丘、寿州、怀远、蒙城、宿州、灵壁、天长、盱眙、泗州、虹县、五河、定远、凤阳和临淮等十八个州县,成为一个跨淮河两岸,占地广大的行政区。
罢建中都之后,作为龙兴之地,凤阳地位仍然非同寻常。洪武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于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所设正留守,位高权重,“例以皇亲协守”,“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此外,凤阳还设有察院巡按行台、河南按察兵备行台等政府机构及一系列皇陵祭祀机构,除此之外,凤阳还是江北四府三州的乡试之地。各类官员合计达一千四百人(《朱元璋与凤阳》),各级吏员总数达数万。
朱元璋还以凤阳作为皇子的教育基地,经常派自己的孩子们回老家体验生活,忆苦思甜。早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就令刚刚十三岁的世子朱标前往临濠谒祀祖宗陵墓,“以知鞍马之勤劳”,“衣食之艰难”,“风俗之美恶”,“吾创业之不易也”。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十月,又命皇太子朱标和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等王子“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洪武九年二月,因秦王、晋王、燕王即将就藩,朱元璋命皇太子带他们前往凤阳,“观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业所由兴”。十月,又诏秦王、晋王、燕王、吴王(后改封周王)、楚王、齐王练兵凤阳。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诏秦王、晋王就藩,仍令燕王、周王、楚王“还驻凤阳”。从此,“诸王之国,皆令诣辞皇陵而后行”,便成为“定例”。为了给皇子提供阅武练兵的场所,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特命驸马都尉黄琛在凤阳独山之前开设一个“广三里”的演武场,令诸王在这里操练二三年或六七年,然后就藩。此后,在洪武十八年,遣湘王朱柏、鲁王朱檀、澶王朱梓就藩,又命蜀王朱椿还驻凤阳,“阅武中都”。
朱元璋还将凤阳用作囚禁犯罪宗室的地方。朱元璋的从孙、朱文正之子朱守谦,因事被朱元璋废为庶人,“使居凤阳力田,冀其知稼穑艰难而思所以保富贵也”。由于这一先例,后来的明朝皇帝,都把犯罪的宗室遣送凤阳囚禁。到明末,此处共关押过一百一十六批皇族。
由于以上种种设施,中都虽已罢废,但这个经济文化本不发达,交通也并非十分方便的凤阳,仍然成为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大明政局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城市,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格局延续到明末,波及清代。
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政策
如何复兴凤阳这块“龙飞之乡”,保护好这块国家“根本重地”,让家乡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让乡亲们生活得好一些,朱元璋没少费脑筋。他为凤阳提供了许多“特殊政策”。
第一条是大移民。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四月那次回乡,给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深深为战争对家乡的破坏而震惊,后来他和大臣们聊起此行的感受说:“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当时史书也记载,“两淮以北,大河以南,所在萧条”,“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元史》卷一八六,《张祯传》),由于“民多逃亡,城野空虚”(《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大片土地荒芜,至洪武改元,凤阳府已是“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在大明开国之际,凤阳县的本地居民仅有三千三百二十四户(《中都志·户口》,引自陈梧桐《洪武大帝朱元璋传》),不到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人。整个凤阳府人口不超过十三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五人。处处残垣,村村寥落,这当然让朱元璋心中十分不舒服。
要复兴经济,首先得有劳动力,为了迅速改变家乡面貌,开国之后,朱元璋在凤阳组织了好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这是明代历史上,政府用行政手段移民数量最多的一次。
除了这次外,比较大规模的还有从山西迁来的移民。洪武六年十月,“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山西北部诸地之人)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
总计洪武年间的移民,达到六次之多,数字大概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这么庞大的数字在明代移民史上乃至中国移民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普通移民外,凤阳还有庞大的驻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总计凤阳府各州县共驻军约为六万四千九百六十人,与家属合计,则有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人。这样算来,洪武年间凤阳府接受的移民总数近四十八万八千人(其中民籍移民三十万,军籍移民十八万八千)。而我们前面提到,洪武之初,凤阳府人口不过十三万。外来移民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倍有余,共占移民后的凤阳府人口总数的80%。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胡干《胡仲子集》,《吴季可墓志铭》)。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第二项政策是减免赋役。洪武十六年,朱元璋有一次闲着没事,再次翻阅刘邦传记,发现刘邦当了皇帝后,曾免了他家乡的赋役。想想自己上次只免了老乡们十年赋役,明显没有刘邦大方,于是再发谕旨:
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了天下,免其丰沛二县之民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凤阳府有福的来做我父母官,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永不课征。每日间雍雍熙熙吃酒,逢着时节,买炷好香烧,献天地,结成义社,遵奉乡饮酒礼。(《凤阳新书》卷五)细细推敲这份圣旨,朱元璋所免的,是“那老的们生在我这块土上”的土著人口的赋役,对外来人口并不普免。另外一份圣旨中,也可以验证这个结论。那是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一道圣旨:
或有人言,亦有非土民当籍土民之时,有等买嘱官吏,诈称土民而在籍者……今命户部差人着落凤阳府,精清土民,非土民者,许里甲人乡人出首到官,赏钞五十锭。诈称土民,治以重罪,能自首者,与免本罪。
原来,由于朱元璋对土著居民实行优惠政策,于是许多外来移民买通官吏,冒充土民,以享受免赋之权。由此更可证明朱对家乡的免税政策只针对自己的老乡,并不惠及外来移民。很多史籍关于这一点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比如《明史》卷三记,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复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谈迁的《国榷》卷七说:“洪武十六年三月甲辰,永免凤阳、临淮二县徭赋。”这一系列记载,都误会了朱元璋的本意。其实朱元璋要突出的,只是他老乡们的特殊地位。
第三则是兴修水利。兴修水利是一项全国性政策,但朱元璋对凤阳的水利建设情况却特别重视。在乾隆《凤阳县志》中记,早在洪武八年,他就特别派两位侯爵康铎、俞春源亲自抓凤阳水利建设。
在朱元璋之后,历代帝王也以凤阳“皇业所基,祖陵所在,视他地方不同”(《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五),在兴修水利上特别重视。
第四是发展交通。朱元璋开辟了从凤阳到南京的驿道,设二十站。整治了“道狭而竣”的清流关,使凤阳的交通条件大大改善。
除了各项特殊政策外,朱元璋在此兴修大量工程,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中都罢建之后,朱元璋还在凤阳继续修建皇陵、十王四妃坟和龙兴寺等,工程浩大,动用人数众多。在中都营建期间,朱元璋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诏建公侯第宅于中都”。中都罢建之后,因为朱元璋鼓励开国元勋们退休回乡,所以公侯府第建设并没有停止。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特赐给公侯每人钞一万锭、银五百两为买木雇工之用,“俾还乡建第宅”。一时凤阳数百里之间,“风云之彦,星罗棋布,于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可谓盛矣”(光绪《凤阳县志》卷十)。大批淮西功臣来到凤阳居住,日常消费巨大,不可避免地带动了凤阳当地商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
朱元璋的特殊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凤阳人口大幅度增加,已经荒芜许久的凤阳土地又出现了“一郡桑麻翠如洗”的兴旺景象。很多荒田被开垦出来,土地数量达到了四十万顷。明代以税粮多少来划分府县等级,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十万石以上为中府,十万石以下为下府。洪武八年,凤阳府在减免了很多税粮的基础上,岁收仍超过二十万石,又成为富庶繁华的上府。凤阳的临淮关“居民稠密,商贾辏集”,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
十年倒有九年荒
然而,谁也没能料到,朱元璋对家乡的特殊关爱,最终却给家乡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恶果。
凤阳的环境,在历代人口压力之下,早已长期恶化。朱元璋的大移民,一时虽给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但如此巨量的移民一下子涌入,却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当时凤阳的土地,最好的部分已经被勋贵圈占,凤阳本地人又占据了中等土地,移民们所获,多是人们挑剩的低产土地。《凤阳新书》卷七说:
“田上则者,归之军,归之功勋矣。中则者,土民括其一,佃户括其一,惟留下则处瘠,乃得以实编民之耕。”卷五又载,移民所获“皆山岗硗确,土石伴错,溪谷流水无有,山林薮泽无存”之地。
没有好地,山地附近的新来移民就上山毁林开荒,对山地的肆意开垦,很快造成了明显的水土流失,挟沙而下的水流,加剧了淮河流域水系生态环境的恶化。
湖边的移民开始围湖垦田。涸湖为田表面上看增加了耕地,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地压力,实则使水利蓄泄失宜,破坏了当地生态的自我循环。
除此之外,凤阳一系列重大工程,又开采了附近山区的大量山林,使许多山变成了童山秃岭。
最要命的是,为了保护祖陵风水,人们进一步破坏了当地生态循环。
位于洪泽湖畔的泗州是明祖陵所在地。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埋在这里。
由于害怕洪水淹没祖陵,导致“王气中泄”,所以自明中期淮患日益严重之后,明政府定下了这样的治水策略:“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
也就是第一是祖陵,第二要保证向北京运送粮食的航道,最后才是老百姓:
“淮域较运道,则运道重。以运道较祖陵,则祖陵尤重。”(《朱元璋与凤阳》)于是明政府经常不顾民生而决高家堰放水,人为降低洪泽湖水位以护陵。这一措施虽然暂时减轻淮河对祖陵的威胁,但使得河道极为混乱,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有明一朝,凤阳周围渐渐变成童山秃岭,森林损毁殆尽,湖泊淤塞,淮河则经常泛滥,水患频仍,两岸百姓民不聊生,“地力既尽,元气日销,天灾流行,人事屡变”(甘山修《霍山县志》卷十三)。凤阳由此十年更有九年荒。“雨三日则沛泽,极目垮洼,泥淖不可耕耘。稍亢阳又为焦土。”
(汪旎修《重修蒙城县志书》卷十一)据《凤阳新书》记载,自万历十七年至泰昌二年(公元年),凤阳共发生旱涝灾害6次,平均五年多一次(《凤阳新书》卷四)。
这只是灾害影响较大的。如果算上一般的灾害,则“凤阳十年九荒,非旱则雨”(《凤阳新书》卷四),至明末更是“十余年来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凤阳新书》卷四)。
当初朱元璋强制迁来的移民的后代,在一次次灾荒中不断逃亡他乡。
比如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凤阳府等处发生涝灾,“田禾无收,积年在彼逃民,俱各转徙,赴济宁、临清各处趁食,动以万计”(《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江淮南北,民多流亡”(《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一)。凤阳的人口,在明中期以后迅速减少。据《凤阳新书》记载,该县“洪武之初,编民十有四万也。自时厥后,旧志尚在丁口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余口,万历六年,则仅存一万三千八百九十四口”(《凤阳新书》卷四,《赋役篇第二》)。
剩下的人,也无法正常定居,许多人渐渐以乞讨为职业。他们“群趋于惰,兼之水旱频仍,中人荡产,且乏兼岁之储。一遇灾荒,辄膏子女、弃故土而适他乡者,比比皆是”(雍正《怀远县志》卷一)。因此形成的“凤阳花鼓”,随着这些逃荒者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而闻名全国。明末清初的魏裔介,曾在一首《秧歌行》里描写说:
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北风吹雪沙扑面,冬冬腰鼓自婆娑。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年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官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燕,如此艰辛实可怜凤阳农业经济因此告别一时的繁荣,重现萧条衰落之状。本来经过朱元璋的大力经营,凤阳府土地数量一度达到了40万顷。至明代中期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该府的耕地面积却回落到仅有61263顷(《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川土》)。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至弘治十五年不足150年的时间,凤阳府的耕地面积竟减少了30多万顷。“凤、淮土广人稀,加以水灾,民半逃亡,二千里皆成草莽。”(《明神宗实录》卷五八)曾任庐州知府和吏部尚书的张瀚对淮河流域的土地荒芜之状有过细致的记述,在经过凤阳一带时,他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荒芜萧条之状。
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寥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涝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三农纪》)直到今天,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既不及苏南富裕发达,也不如鲁中的蓬勃兴旺,同为沿海开发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当地生态环境在明代遭到了严重破坏。朱元璋当初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一片好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