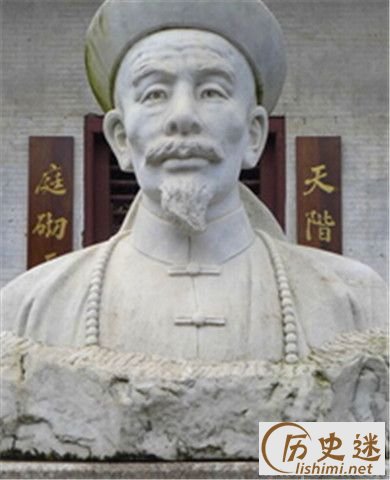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冰心评徐志摩)
冰心一定想不到,在她七月三十日写了那首有点“莫名其妙”的诗歌《我劝你》之后三个多月,就再也不用劝谁了。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去世。
对徐志摩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对冰心来说,这是一次打击。冰心和徐志摩年龄相仿,当时都很年轻,又都是名声在外的诗人,原本有些惺惺相惜。谁能想到徐志摩骤然离世呢?他才33岁啊——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恰好在这个时候,她给梁实秋写了一封信,而恰好这封信后来被公开出来,成为谈资。
冰心当时的态度也许有些过激。无论是谁,想到身边相熟的朋友年纪轻轻遭逢大难,情绪上多少会有一些不冷静。于是就有一些好事者根据只言片语,渲染出一些奇怪的事情来……
(一)徐志摩:冰心今天“声声志摩,异哉”
同为文坛上声名鹊起的领军大将,徐志摩和冰心早就认识了,但两人的来往可能不多,也不很热络。
1928年12月23日,徐志摩在陇海线途中给陆小曼写信(上一封信是12月13日,写于北平),其中提到冰心:“晚归路过燕京,见到冰心女士;承蒙不弃,声声志摩,颇非前此冷傲,异哉。”
在这篇两千字的长信中,就只是随口这么一句,可见遇到冰心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徐志摩所奇怪的,只是冰心此前对他的态度可能比较“冷傲”,而这次竟然“声声志摩”,热情了不少,反而让徐志摩有些不适应。
这一年徐志摩31岁,冰心28岁,于次年与吴文藻结婚。
冰心和吴文藻
对徐志摩来说,192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在大学中的教授工作暂且不提,他还创办了《新月》月刊,他最著名的诗歌《再别康桥》就刊载于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也就是说,可能冰心在这次见面前不久才读到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好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冰心是因为这首诗才对徐志摩有了好印象吗?我们不知道,暂且作为一个小小的“悬案”吧。
之后冰心还在徐志摩的书信中出现过一次。1931年6月16日,徐志摩在北平给“我至爱的老婆”陆小曼写信,提到这天“午刻在莎菲家,有叔华、冰心、今甫、性仁等”,莎菲是陈衡哲的笔名,其丈夫任鸿隽是当时中国响当当的人物。四位客人也都是现代史上的名人——凌叔华、冰心、杨振声、沈性仁,再加上徐志摩,这小小的聚会也显得光芒四射了。
徐志摩这次连与冰心的交流都没有提,只是抱怨“应酬真烦人,但又不能不去”。这倒好像把冰心也归入到“真烦人的应酬”之列了。
此时离徐志摩去世还有五个月。
左冰心,右林徽因
(二)冰心: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
相比徐志摩把冰心的位置放到某个边缘角落,连提都没兴趣多提,冰心对徐志摩的态度似乎有些过于激动。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去世,11月25日,冰心写了一封信给梁实秋。徐志摩失事未久,冰心可能还沉浸在震惊之中,因此这封信读起来就有其奇怪:冰心一边在信里说“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一边谈了徐志摩不少,甚至说徐志摩对她说,“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态度和内容显然超过了泛泛之交的程度。这封信不用多分析,直接就能看出冰心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们直接将有关徐志摩的前半部分放在这里吧:
实秋:
你的信,是我们许多年来,从朋友方面所未得到的,真挚痛快的好信!看完了予我们以若干的欢喜。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看他“自剖”里的散文,“飞”等等,仿佛就是他将死未绝时的情感,诗中尤其看得出。我不是信预兆,是说他十年来心理的蕴酿,与无形中心灵的绝望与寂寥,所形成的必然的结果!人死了什么都太晚,他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他真辜负了他的一股子劲!
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也很难说。
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到这里,我打住不说了!
梁实秋像
(三)哪里来的涟漪
既然和徐志摩不是朋友,那么怎么又表现得如此激动?
2012年,《意林》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冰心可曾恋过徐志摩》。文章中说:“这个风一样的男子,还是在冰心心里荡起了一阵阵的涟漪。”根据就是上面这封给梁实秋的信。
这篇文章不能说完全空穴来风,但也只能算捕风捉影。在谈及这些个人经历、私人情怀时,要尊重作家个人的表述。既然冰心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她对徐志摩主要是“怜惜”之情,还扯什么“风一样的男子”、什么“涟漪”呢?冰心此时身为人母,如果对徐志摩有什么非分之想,难道还会堂而皇之地把这些不伦之言写给梁实秋看吗?冰心作为世纪老人、中国当代文坛重要作家,当代的年轻朋友们贸贸然提出这么个问题,本身就是对冰心的不尊重。再说难听一些,也就是“欺负”老人家已经过世,不能发言来批驳这些奇谈怪论了。
冰心
冰心在谈到徐志摩的时候,主要有两点感慨,其一是他在诗歌上的天才没有完全地发挥出来,这是作为诗人、作家的惺惺相惜;其二是徐志摩深陷感情旋涡之中,未能处理好与各位女士之间的纠葛。
徐志摩的情感经历此处不再赘述,问题在于,冰心似乎并没有像其他的许多人一样,认为徐志摩是负主要责任的一方,她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女人误他?”“他误女人?”
对绝大多数的徐志摩研究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徐志摩对张幼仪的冷漠,难道是张幼仪误了他吗?徐志摩苦苦追求林徽因,难道是林徽因要求的?即使因为陆小曼的生活习惯常常为人所非议,但要注意的是,徐志摩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可以看做是主动一方,陆小曼是被追求者。
左:林徽因
这也使我们在多年以后回顾徐志摩的情感经历时,不得不承认,即使陆小曼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徐志摩也是心甘情愿地供养着她的。虽然有怨言,但他甚至连和陆小曼离婚的念头都没有。
但冰心不理这些,冰心就是觉得,徐志摩身边的女性也对徐志摩的“不争气”负有责任,而且是相当重要的责任。她在《我劝你》中写道:
“别忘了他是个浪漫的诗人。/不说了!你又笑我对你讲圣书。/我只愿你想象他心中闷火般的痛苦,/一个人哪能永远胡涂!/有一天,他喊出了他的绝叫,哀呼。/他挣出他胡涂的罗网,/你留停在浪漫的中途。/你也莫调弄着剧意诗情!/在诗人,这只是庄严的游戏,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
诗人是浪漫的,也是痛苦的,诗人因为这段胡图的感情而“绝叫,哀呼”,而“你却逗露着游戏的真诚”。那么这首《我劝你》是在劝谁呢,很显然不是劝这个痛苦中的诗人,而是劝这个捉弄诗人的女人。就像她在诗的一开始就说的:“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虽然我晓得/只有女人的话,你不爱听。”
这就扯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了:后来的旁观者往往对陆小曼不满,冰心却认为最该被批评的不是陆小曼,而是林徽因。
林徽因与梁思成
(四)谁知道她俩怎么了
与其说是冰心对徐志摩有什么涟漪,不如说冰心对林徽因有所不满。
1933年,冰心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我们太太的客厅》,明确地将这种不满表达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太太”将诗人、哲学家、科学家等等人士都“玩弄”于股掌之间,通常认为这位“太太”正是以林徽因为原形。而“太太的客厅”中那位卑躬屈膝的“诗人”,则被认为暗示着徐志摩。
冰心写道:诗人在见到我们太太时,“诗人微着身,捧着我们太太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诗人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徐志摩的情诗《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到你的波心”。
林徽因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回应了冰心的这篇文章:她送给冰心一坛山西老陈醋。
林徽因
回头再看,如果冰心真的对徐志摩有涟漪,她恐怕不会把徐志摩塑造成这个模样,甚至根本不会以徐志摩为蓝本来塑造这个不怎么正面的诗人形象。1931年10月,林徽因搬进北总布胡同3号,所谓“太太客厅”就是发生在这里,后来金岳霖称之为“星期六碰头会”。搬入的次月,徐志摩即遇难,那么徐基本没有参与到所谓“星期六碰头会”之中。冰心只不过是借这位诗人来讽刺太太,这再明显不过了。
冰心与林徽因早早失和,大约是导致冰心写出《我劝你》《我们太太的客厅》以及致梁实秋之信件的主要原因。至于失和究竟又有怎样的原因,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说清楚,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猜测。
林徽因1927年毕业于宾州大学美术系
1926年,冰心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成回国。之后数年间,冰心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大事,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结婚,并于1931年2月6日生长子宗生(吴平)。1930年1月,母杨福慈病逝于上海,1931年6月30日,冰心完成纪念母亲的长篇散文《南归》。在家事上,冰心已经不是那个心怀浪漫的女作家了。
这几年的政治局势也呈现出风雨欲来之感。在冰心写下《我劝你》的1931年,就发生了各种震动文坛的大事。本年度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左翼作家在上海就义,2月,巴金发表长篇小说《家》,3月,日本军人为发动侵华战争造舆论,9月18日,爆发“九一八”事变。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中国的局势都出现了剧烈变化,那么,冰心的思想发生转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过去的受到宗教教义影响和略显浅薄的所谓“爱的哲学”逐渐淡化,作品中的现实性有所增强。对冰心来说,这是精神境界上的巨大提升,她已经能够真正睁眼看待这个并不完满、充满血泪的世界。一般认为在1931年,冰心发表《分》以后,就进入其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冰心的思想境界发生较大转变时,她对徐志摩乃至林徽因等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社会影响产生一些不良的观感,也就很自然了。
冰心的这些观感,并不意味着林徽因等人就应该被否定。冰心恐怕没有意识到,她和林徽因等人的差异主要并不在于是否对国家、民族产生责任感或危机感,“我们太太”并不是不关心国事、家事甚至一味纸醉金迷的逃避者,在抗战期间,林徽因等学者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对中国文化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这一方面冰心似乎忽略了——她以诗人的身份要求自己和徐志摩,却没有注意或者不愿把林徽因首先定位为一个兼通中西的学者,而学者在所具有的社会参与程度天然较为薄弱,这和单纯的作家有所不同。
左冰心,右林徽因
简言之,冰心对林徽因等人的定位产生了偏差,再加上相对比较保守的生活态度,使她难以认同林徽因等人与社会、政治相对较为远离、较为隔膜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说这就直接导致了二人的反目,但想必还是导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冰心的《我劝你》《我们太太的客厅》,恐怕都与这样的心态有丝丝缕缕的关系。
冰心对徐志摩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徐志摩诗情、诗才的欣赏,而她对徐志摩的痛心以及对林徽因等人的不满,直接导致两位优秀女性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当然,这对二人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影响并不是很大,也几乎不涉及对双方的历史评价。这些只是小小的谈资,丰富了我们对作家本人生活经历、情感变化的了解罢了。
林徽因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免责申明:本站所发布的文字与图片素材为非商业目的改编或整理,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或涉及违法,请联系我们删除,如需转载请保留原文地址。